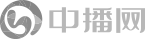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。
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,目送我走向远方。
但我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。
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。
我轻轻地笑着,并不出声。
我让那些早早上路的马车,沿着我的堤坡,鱼贯而行。
那些马车响着刮木、像奏着迎神的喇叭,登上了我的胸脯。
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。
那些裹着冬装的唐古特车夫也伴着他们的辕马,
谨小慎微地举步,随时准备拽紧握在他们手心的刹绳。

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。
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。
是的,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。我是滋润的河床,
我是枯干的河床,我是浩荡的河床。
我的令名如雷贯耳。
我坚实、宽厚、壮阔,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。
我创造,我须臾不停地,
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。
我刺肤纹身,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。
我喜欢向霜风透露我体魄之多毛。
我让万山洞开,好叫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。
我是父亲。

我爱听秃鹰长唳,他有少年的声带,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。
他的翼轮双展之舞可让血流沸腾。
我称誉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猎人。
也同等地欣赏那头三条腿的母狼。
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。
也永远怀念你们——消逝了的黄河象。
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。
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。
我是屈曲的峰峦,是下陷的断层,是切开的地峡,是眩晕的飓风。
是纵的河床,是横的河床,是总谱的主旋律。
我一身织锦,一身珠宝,一身黄金。
我张弛如弓,我拓荒千里。
我是时间,是古迹,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。
是始皇帝,

我是排列成阵的帆墙,是广场,是通都大邑,是展开的景观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,
是结构力,是驰道,是不可克的球门。
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。
而现在我仍转向你们白头的巴颜喀拉。
你们的马车已满载昆山之玉,走向归程。
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胝掌准时地亮了。
你们的团圞月 正从我的脐蒂升起。
我答应过你们,我说潮汛即刻到来,
而潮汛已经到来……